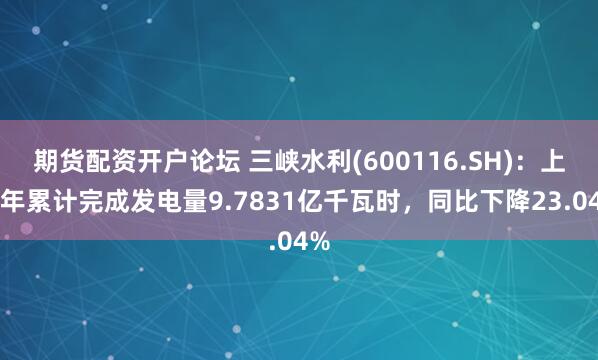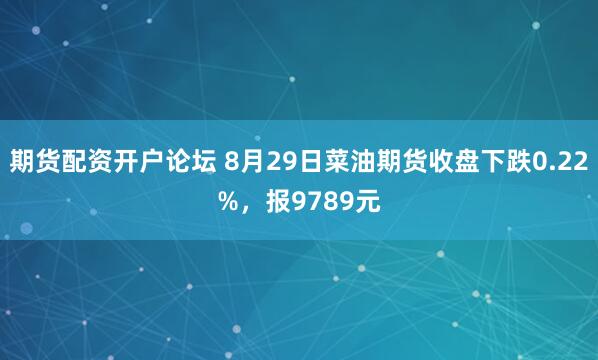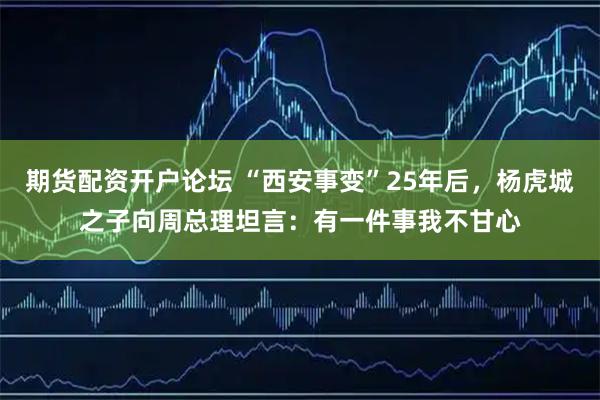
“总理,有句话,我憋在心里很多年了。”1961年12月,一场纪念“西安事变”25周年的招待会刚刚散去,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,眼眶微红,终于对周恩来吐露了心声。周总理温和地看着他,示意他讲下去。杨拯民声音有些颤抖:“多少年来,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期货配资开户论坛,有一件事,我总是不甘心……”

这桩让英雄后代耿耿于怀、意难平了二十多年的心事,根子,其实在一本书上。一本由蒋介石亲自口授、由他的“文胆”陈布雷代笔炮制,后来流毒甚广的《西安半月记》。
要说这事,还得回到1936年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天。事变和平解决,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,惊魂甫定之余,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回“面子”。他把陈布雷叫来,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指示:写一篇对张、杨的训词。蒋介石特别强调,张学良是“年幼无知”,被利用了,而杨虎城,才是真正的“肇事元凶”。这番定调,充满了政治算计和个人泄愤,为后续的一系列舆论操作埋下了伏笔。
紧接着,蒋介石卧床养伤期间,又给陈布雷派了个更棘手的活儿——代写《西安半月记》。名义上是让世人了解事变经过,实际上,就是要按照他的口径,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深明大义、感化叛将的领袖,而将张、杨二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陈布雷当时根本没去西安,手里一丁点材料都没有,只能硬着头皮,靠着蒋介石的口述和几篇日记,在杭州一家旅馆里闭门“创作”。大年三十,万家团圆,他却在房间里绞尽脑汁,为一篇彻头彻尾的伪史耗费心神。这本一万多字的《西安半月记》出炉后,果然被国民党当局当成“权威史料”大肆刊印,一时间洛阳纸贵,颠倒黑白,将一场逼蒋抗日的爱国壮举,歪曲成了个人野心驱动的犯上作乱。

正是这本白纸黑字的书,像一根刺,深深扎在杨家人的心里。父亲杨虎城为国奔走,最终惨遭杀害,连家人都未能幸免,到头来还要背负如此污名。试想一下,这让作为长子的杨拯民如何能够甘心?他所不甘的,不仅仅是家族的荣辱,更是历史真相被肆意践踏的愤懑。
而周恩来,恰恰是那个最理解并始终支持他去拔掉这根刺的人。

其实,早在1946年,也就是“西安事变”十周年之际,延安召开纪念大会,周总理就特意安排杨拯民上台发言。会前,周总理对杨拯民说,自己身份特殊,有些话不好说得太重,让他放开胆子,好好痛骂一下国民党反动派。杨拯民拿出准备好的稿子,周总理看过后,还亲自动笔,帮他加重了一些语气,使其更加犀利。大会上,周总理率先义正辞严地谴责蒋介石,要求释放张、杨两位将军,把全场气氛点燃。随后,杨拯民上台,将十年来的悲愤与不平一吐为快,效果极好。
到了1949年,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,杨拯民随代表团抵达北平。周总理设宴款待国民党起义将领,也特意叫上杨拯民作陪。席间,周总理拉着他的手,向傅作义等一众来宾郑重介绍:“这是杨虎城将军的儿子。”宴会后,杨拯民忍不住向总理打听父亲的下落,周总理当即在客厅里大声询问在场的原国民党人士,谁知道杨虎城先生的近况。这份关切,溢于言表,是装不出来的。

不久后,重庆解放,杨虎城将军遇害的噩耗传来。杨拯民悲痛欲绝,第一时间请示周总理。周总理的指示沉重而坚定:“这不是你的私事,是党交给你的任务。要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,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。”在周总理的亲自关照下,一场声势浩大的公祭活动,从重庆沿江而下,直抵西安,让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所以,当1961年杨拯民再次提出,应该整理史料,批驳那本颠倒黑白的《西安半月记》时,周总理当场拍板:“你这个意见很好,最好由三方面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,把它搞出来。”他深知,为英雄正名,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,更是对历史的负责。

周总理对杨拯民的关怀,远不止于为其父正名。这份情谊,更像是父执,是严师,也是良友。杨拯民一生都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场景。那是1937年的西安,他还是个少年,从门缝里偷偷看父亲和“周胡子”谈话。谈完事,周总理看到门口的他,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,快步上前亲切地拉着他的手,询问他的情况。那种发自内心的平易近人,让接触过太多国民党达官显贵的杨拯民,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他暗下决心:这才是真正伟大的人物,我要跟着这样的人走。
新中国成立后,杨拯民转业去搞石油。周总理深夜在西花厅接见他,开口便问:“有人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不合适,是否有此事?”杨拯民坦言自己愿意去一线,不怕艰苦。周总理听后十分欣慰,鼓励他说:“要想做成一件事,还是要吃大苦,耐大劳。”寥寥数语,既是关怀,也是期许。后来,杨拯民在北京开会,晚会上偶遇总理,周总理拉着他,一连串问了好几个关于西北石油的专业问题,问到最后,竟把在一线干了好几年的杨拯民给问住了。杨拯民事后感慨,总理为国家的石油工业,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。
遗憾的是,由于后来的特殊历史时期,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的“西安事变”史料整理工作,未能及时开展。但这并未减损周总理在杨拯民心中的分量。1966年春节,杨拯民在天津见到周总理,两人还一起打了乒乓球。那天总理兴致很高,谈起生死,他说:“人,不要怕死,我想,死最好是打仗和敌人拼,一粒子弹结束生命。如果不打仗,那就拼命工作。什么时候消耗完了,就结束生命。”

这番话,仿佛是他一生的写照。对杨拯民而言,周总理的形象,早已超越了一位普通的领导人。正如他晚年在回忆文章里所写:他是我的父执,可是从来不以父辈自居;他是我的良友,他的关怀给我温暖;他是我的严师,教我清清白白做人,老老实实做事。他的高尚品德令我倾心,他的言行典范促我效仿。这段跨越了近四十年的深厚情谊,本身就是对那段风云激荡历史的最好注解。
美港通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